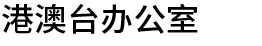【编者按】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首任院长阮昕,以及交大设计日前全面启动的建筑学、工业设计工程、风景园林三个专业硕士(国际)项目,有方的读者应已不陌生。 项目招生开放至今,这一“国门内的全英文国际化设计教育”,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在10月31日网上报名截止前,通过以下11个提问,走近院长阮昕理解中“对标国际”的判断标准,及中西设计教育之间的共性与微差。
【名师名言】
Q&A
有方 在上次有方专访后的这一年,您提到的《浮生·建筑》一书,“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规划建筑板块”展览,“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以及设计学院的国际项目,都或者顺利完成,或者有了实质进展,可以说是“动作频频”。除了它们,最近又“邂逅”了哪些事情?
阮昕 很有意思,一年之后又从“邂逅”谈起,而你说的这几件事确实是在逐一推进。去年11月我们组织召开了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讨论对于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设计教育能够如何应对?当时提及最多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地缘政治、资源分配不均——谁也没有想到会有“新冠”,所有重大事件都被它打断、很多问题都要重新考量。
“新冠”发生后,我们的教学逐渐演化为轰轰烈烈的线上学术交流。比如说建筑学系的“青交建筑论坛”,邀请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在这个平台上展开交流,与我们的师生谈谈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这个系列也被称作“青交吐槽会”,大家都很坦诚,面对问题有一种幽默的态度,放下了些传统学术里“教”与“学”不平等的关系。在此之外的大型活动还包括邬达克讲堂,与上海市风景园林学会共同举办的风景园林大师讲坛,以及创新设计“大家”谈等。
近期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设计实践导师(Teaching Fellowship)的招聘,后来应聘的人非常多。在制度上我们能让这些老师成为交大的一员,是合同制,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来设定设计教学题目。虽然近期的课程都是在线上,但最终效果也非常好,设计实践导师几乎成为了我们专业教学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所以,虽然“新冠”好像彻底改变了生活,但新的邂逅还是很多;包括我们的新聘实践型教授庄慎老师,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建筑师加入到我们的教学行列里。可以说,很多事并未因“新冠”而停滞。
有方 您觉得疫情后普遍的线上交流,会对学术态势带来什么长期的改变吗?
阮昕 首先,线上交流的受众面之大,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我们此前举办的线下学术活动,除非是学术明星、明星设计师主讲,否则经常会担心没有人来听,总要组织学生或者同事。而在线上,像最近我主持的孟建民院士、孔宇航院长的邬达克讲座,轻轻松松就能有几千人参与。我觉得这是一道全新的风景线。
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是线上无法取代的。比如在我们9月组织的线上讲座“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中国园林文集》编纂史与新视域”中,因为主讲嘉宾Alison Hardie与我有很多共同的故交,过程中既谈学术、又叙旧、偶尔也穿插到其他的事情,就会感到线上沟通终归有些隔阂。此外,当我在线上授课,即便是已教了十多年的“住宅历史”,还是会感到线上的局限:如果不能看到学生的眼神,不能感受到教室里的气氛,我有时就会讲得“非常努力”而没有足够的停顿,学生浸润其中的理解就会变得略为困难。这就像是看话剧和看电影的区别。
线上的文化交流,于我而言像是bittersweet苦乐参半。我相信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是永远无法被完全取代的。尽管现在看来,“新冠”很可能会跟我们长期为伍,但人际线下的交流一定会复归,而且大家会愈加珍惜。
有方 交大去年主办的设计教育理念国际研讨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即将展开教学合作的院校学者之间的一次交锋。这次研讨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论点?是否及如何影响了后续国际项目的组织?
阮昕 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活动前的设想:通过自由的交流对谈,把希腊传统的“symposium”延续下来;在轻松的氛围下,每个人事先思考过主题后再发言,期间其他人不要打岔(笑),发言结束后大家再提问。会议前大家有点担忧,怕这样做会导致讨论松散,收获不如目前学术研讨中常见的“演讲”模式多。但事实上,这种顾虑在活动开始不久后就打消了,最终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会后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对于几个核心问题——比如设计教育是否能对当代面临的挑战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而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全球化是否是不可挡的趋势(当时还未经历“新冠”带来的颠覆性隔绝),但同时也会带来资源和机会的不公?——从道义的角度讲,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识。但因为地缘政治、技术语言、资源条件不同等种种原因,在实施层面的方法上,大家的思路可能很不一样。
会议结束后,可以将交大设计想做的事情总结为:“体用并举,设计大义”。体用并举,可以具体地理解成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以自然地延伸到中西文化的交流上,也可将之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亦即“道器并举”。培养专业人才,是我们学科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归根结底,从中国文化的教育来讲,我们的目的是春秋大义,设计大义——最后讲的既是道德,也是美学,品位,人生态度。这次会议给了我们厘清设计教育理念的机会,又在具体的操作上提供了课题。
有方 回到本次专访的主题:今年交大设计全面启动的专业硕士(国际)项目。在您的理解中,相较国内外同等级高校的硕士培养,交大项目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阮昕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开始筹划国际专硕项目的时候,没有人能预见“新冠”大流行会给全球化带来这么大的挑战,中国学生出国会变得困难重重。而今日,在中国本土办国际项目、做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就全部体现出来了。我们三个项目中的工业设计工程(IIDE),在今年9月已启动教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国际专硕,则将于明年9月开始。
全英文授课、外聘国际顶尖高校教师前来交大授课,是项目最明显的突破。校企合作是另一个重要特色,比如IIDE项目已与阿里、华为、小米、上汽等重要企业携手办学。建筑学和风景园林项目也有这个特点,区别在于学院与行业的结合是通过设计实践导师制度和具体的教案设计实现——因为在这两个专业,“企业”的定义相对模糊。
此外,三个学位有一个共享的背景,就是长三角一体化。“大上海”是我们操作的具体环境,超大高密度城市的设计提升是我们的重要议题。前段时间住建部和上海市有一个合作框架,叫作“超大高密度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现在我们正与交大国务学院、城市治理研究院合作,研究超大高密度城市精细化管理所需要的设计提升——如果没有设计,城市管理就可能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难有具体落实。以上,是我理解中交大设计国际专硕的特点,也是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
有方 您如何理解对于项目“国际化”程度的判断标准?
阮昕 国际化的定义确实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上次专访里我们讨论过,院系调整后的上海交大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重振雄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走了国际化的道路。而对于学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在国际化的层面上,对品质做出判断?这种判断,首先要选择真正恰当的准则。
对于今日中国的设计教育,如果看我们学生画的图、参与的国际交流、在国际竞赛中的获奖率,以及中国设计师在期刊刊登的漂亮照片等等,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中国的设计教育水平还蛮高的,已经不错了。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中国城市建设的品质,看看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住宅小区、公共设计、道路管网上下水等基础设施的品质和安全性……如果从这些层面上做品质的判断,我们似乎没有太多可骄傲的地方。我们的设计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的国家战略提到长三角一体化,要在超大高密度城市的基础上做精细化管理,而光谈管理没有设计的精细化是肯定不行的,很多方面要通过设计来提升。“国际化”不全等于要把学生送到美国欧洲,也不仅指将国外师资引入中国,以城市环境的品质为判断标准,“对标国际一流”才能有实在的含义。如果想在这个层面上做好,首先要有平视的态度、平和的心境;对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国外的发展,要避免仰视和鄙视这两种极端的态度。过去,我们似乎仰视得比较厉害,而现在我担心鄙视的势头会有上涨,要特别警惕。
有方 也就是说,“设计教育”的一流与否,还是要看我们的城市人居环境是否有品质上的改善。
阮昕 对。如果忽略了这个,“设计教育”就有点自娱自乐了。
不同历史阶段的优秀城市环境,往往是在一定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基础上,人居模式与城市空间达到的极好平衡。由此才有威尼斯这样的,我们至今依然能够回味欣赏的城市艺术品。我想,今天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现在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有方 这一希望落于实处的国际化目标,具体将通过怎样的培养机制实现?
阮昕 具体来说,首先是兼收并蓄,然后渐渐做到以我为主。操作层面上,国际专硕项目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有接近一半的课程是外请合作院校的老师来教授。而“以我为主”不是妄自尊大,是指三个项目要有对自己特色和定位的清晰认识,基于交大、上海、长三角的背景,找准自己的方向感。
如果能厘清“对标国际一流”的实质要求,并兼顾“兼收并蓄、以我为主”,则具体操作中即使有困难,也应是可克服的。
有方 三个项目希望培养出怎样的学生群体?将如何在您一贯关注的职业技能培养与人文通识教育之间,取得平衡?
阮昕 交大设计的教育理念和具体操作,可总结为“体用并举、设计大义;以体为道,以用为器”。在这个原则下,职业技能与人文通识之间的平衡,确实是我们培养的重要目标,当然这个平衡也一定是动态的。
对人文通识或者说道德的培养无疑重要,但一定要具体化,否则就很容易流于空泛、让学生产生抵触。在具体化后——比如说当“可持续性”同时成为一个文化/道义/技术问题,讨论就会变得很有意思,能将道义与专业技术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设计教育中的人文通识层面能做到的,在这个基础上才得有品位——如果设计教育仅将“品位”理解为一种视觉倾向,则无疑是种危险的误区。
而专业的职业技能,是设计教育的看家本领。其所指,要分学科进行具体的讨论和定义,认识到什么是我们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基本功。
有方 三项目中的工业设计工程(IIDE)已于去年启动招生,第一届报考情况如何?迄今收到了来自师生的哪些反馈?
阮昕 第一届新生已于今年9月入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学习。虽然去年的招生工作有些仓促,但这届学生的综合素质之高,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可能跟“新冠”带来的国际形势转变有关,也可能跟我们的课程设置理念有关:具体来说,IIDE就是把设计提高到通识的层面上,不再把工业设计限制在产品设计的层次上。这是一个“虚实结合”的专业,它面对的既有实实在在的产品,比如一个手机、一段程序,同时也包含虚拟的无形的东西,将人和人、物、空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智能科技的、社会生活品质的层面上,都体现出来。
运行至今,学生目前处在好奇而充满热情的阶段。最近我们和上汽、阿里等企业合作,做了一系列工作坊和设计周:上汽有一整个团队每周前来授课,而近日举办的阿里巴巴设计日也是以IIDE为主导,阿里的设计师们有私下反馈说看中多位同学,希望未来能到阿里就职。
对于校企合作,我们希望学生知道这是“理应如此”,而不仅是因为专业硕士是目前政策倡导的一个方向。过去的学术硕士,可能在无形中拉开了学术科研与具体行业的距离,但实际上行业跟大学是一定要有合作关系的:大学的天职一是完成知识的延续传承,二是探索真理、实现知识的创新;同时,行业也不仅是现有知识的使用方,不仅扮演着“知识回收”的角色。当下的成功企业往往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方面也做得很好,以华为为例,对R&D的投资巨大。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互学习、相互刺激,推进大学与行业的合作呢?
目前来看,我们的学生对这点是完全理解的,能感受到校企合作带来的机会。让学生理解我们的教育理念,是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一个成功的学位项目,定然是师生合作的结果。
有方 去年专访谈到国际项目时,您最后的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长远来看,也希望让更多的国际学生融入到这个格局中。在知识阶层,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面对的一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未来。”
今年的疫情,可能让很多人第一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真切的认识。您觉得这次疫情对国际文化生态,会有什么长期影响吗?
阮昕 这是我最近常想到的问题,一个原因是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将近30年,而现在中澳关系面临着考验。去年不知为何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个话有些“讲重了”,但在今日却格外真切。
对于未来的全球文化合作,我依然是乐观的。因为知识阶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是更加坚定的。但现在面对的考验也更大,因为目前西方还有一个类似辜鸿铭老先生曾指出的“盲民”(the mob)的阶层,主流政治导向对他们的影响会非常大。很多国外同行会觉得这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以美国为例,这个阶层如果占比近30%、40%,考验将是巨大的,因其不能做到历史地、客观地、文化地看待问题。
在今日回顾去年谈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自诩为知识阶层,能够通过对人才的培养等途径带来一些影响、有所践行,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有方 无论是交大的国际项目,还是新近公布的您将担任中欧建筑奖评委会主席、首届中欧建筑邀请展学术委员会成员,可以说国际对话始终是您致力于的一个方向。采访的最后希望了解,您如何理解设计教育领域,文化沟通的意义?
阮昕 好像都是偶然的事件,都不是“规划”来的,但又恰好都与文化间的沟通交流有关。不久前在ArchDaily发布的一个采访,问我“为什么中西交流是我感兴趣的事”,回忆后我发现这也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从前因为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知甚少,所以都想学习,自然就带来了比较。
在我的理解中,文化间沟通的意义就类似于钱锺书先生所讲的“打通”,这是“比较”的目的。钱老先生给自己想了一个英文的说法,striking the connection,听起来更耳目一新些(笑)。在“打通”的过程中,需要比较对象的“共性”与“微差”;在共性之外,对不同文化背景中微差的辨析,才是“打通”所追求的目标。
回想最近在国内跑的地方,从旅馆房间里看出去,千城一面。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城市的情况,是我们设计教育者要面对的现实。在这个层面上看,略有些伤感。我们的出路是什么?今天还会重建一个从元大都开始到明清的北京,重新创作出一个威尼斯吗?但细想又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仔细挖掘,或许还是能见到千城一面背后微妙的地方性。一个通俗的例子是,我最近老坐飞机,也常是东航;而东航的那碗面,在上海是上海的做法,到了昆明用的咸菜和辣椒就不一样,再到温州就变成鱼丸面了。都是东航的一碗面,但也能有这种微殊的地方性;而在设计教育与交流里,这微差尤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
【名师名片】
阮昕,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首任院长、光启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建筑环境学院副院长、建筑系主任(2004-2018),悉尼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2002-2004)。现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建筑评论家委员会委员、美国建筑历史学家学会会员、澳大利亚建筑师学会学术会员、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同济大学顾问教授